在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版图上,香山文化如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,承载着海洋文明与农耕文明的交融记忆,孕育着开放包容、务实创新的精神基因。从这片土地走出的近代思想家、实业家郑观应,其经世致用的思想和实践,一方面根植于香山文化开放包容创新的土壤,另一方也极大地丰富了香山文化的内涵。

11月1日,中山市香山书院“遇见先贤”系列课程走进三乡镇,广东历史学会副会长、历史学博士胡波以《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知和行》为题,向市民读者讲述香山文化与郑观应之间相互成就、深度交融的历史脉络,也为这份珍贵的文化资源在当代的传承与发展提供了深刻启示。
 香山文化始终是“活的文化”
香山文化始终是“活的文化”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,一方人又塑一方文。
香山这片北接珠江、南临南海的土地,曾是海洋与陆地的交界地带,早期先民在这里围海造田、晒盐捕鱼。历史上的多次移民浪潮,又带来了闽南人、客家人等多元族群,他们在语言、习俗、生产方式等方面相互交流碰撞,形成了包容共生的社会生态,以及逐步从海洋文明向农耕文明过渡的文化形态。
“这种转型不是断裂式,而是一种交融式的共生。”胡波教授指出,这种独特的历史进程,让香山文化既保留了海洋文明的冒险开拓精神,又兼具农耕文明的务实稳健特质。这里的人们既善于驾船出海、闯荡南洋,在商贸往来中汲取世界文明成果,也重视土地耕耘、家族传承,在烟火气息中坚守文化根脉。

明清以后,葡萄牙人定居澳门,西方的宗教、科技、艺术在此传播,与本土文化相互激荡;而香山籍华侨远赴海外,又将异域文化带回故土,形成了中西合璧的文化格局。至此,香山文化融会了内陆文化与海洋文化、岭南文化与中原文化、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等多元文化的精神特质。
“这种开放的文化环境,孕育了香山人和而不同的包容心态。”胡波教授表示,不同族群之间尽管语言不同、信仰不同,但环境要求他们对异质文化给予了理解、接纳的态度。
2002年,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郑观应诞辰160年大会上,胡波教授首次提出“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知和行”命题,“香山文化”这一概念也引发了海内外专家的共鸣。2022年,中山、珠海、澳门三地广泛开展庆祝香山建县870周年系列活动,进一步推动香山文化深入人心。
“香山文化最可贵的地方,在于它始终是‘活的文化’,从明清的商贸文化到近代的洋务思想,再到当代的湾区精神,它一直在随时代演变,却从未丢失核心基因。”胡波教授强调。
 郑观应是连接传统与现代、
郑观应是连接传统与现代、
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式人物
香山文化不仅塑造了香山人的精神品格,更孕育了孙中山、郑观应、容闳等一批影响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杰出人物。他们带着香山文化的烙印,在时代浪潮中勇立潮头。
1842年,郑观应出生于三乡雍陌村,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,本土的风俗习惯、家族教育、社会氛围深深烙印在他的思想深处。科举考试失利后,郑观应在父亲与乡邻的引荐下,远赴上海投身洋行,开启了商业生涯。

在上海的数十年间,郑观应从洋行职员成长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,他先后在太古轮船公司、招商局等机构任职,涉足航运、矿业、铁路、电信等多个领域,成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先行者。在商业实践中,他既坚守香山商人诚信经营的传统,又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,提出了“商战为本”的经济思想,主张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列强竞争,改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地位。
胡波教授认为,这种将传统商业智慧与近代经济理念相结合的思维方式,正是香山文化兼容并蓄特质的生动体现。
此外,郑观应较早“拿起笔”,在思想领域留下《救时揭要》与《盛世危言》等代表著作。他既批判封建专制的弊端、揭露社会积弊,又系统提出了学习西方先进技术、改革政治制度、发展教育事业、加强国防建设等一系列救国方略。他主张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但又突破了洋务派的局限,强调不仅要学习西方的器物层面,更要借鉴其制度文明和思想文化。
值得注意的是,郑观应的一生始终没有脱离香山文化的滋养与同乡群体的支持。在上海打拼期间,他依托唐廷枢、徐润等香山籍买办形成的商业网络,获得了重要的发展机遇。同时,他又突破了地域圈层的局限,主动与盛宣怀等洋务派官员交往,与外国传教士交流。这种可贵的“天下观”,让郑观应成为连接传统与现代、中国与世界的桥梁式人物。
不过,胡波教授也指出,郑观应的人生也充满了时代的矛盾与挣扎。他认为,郑观应的困境是时代的悲剧,也是香山文化内在张力的体现。一方面,儒家正统思想让他对清政府抱有幻想,不愿彻底革命;另一方面,开放视野又让他看清体制弊端。“这种矛盾不是他个人的问题,而是整个近代知识分子的集体困境。但即便如此,他从未放弃救国初心。”胡波教授表示。
 文化基因与人生实践的“双向奔赴”
文化基因与人生实践的“双向奔赴”
在胡波等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中,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关系是“双向奔赴”的共生:“不是文化单方面塑造人,也不是人单方面成就文化,而是相互滋养、彼此成就。香山文化给了郑观应成长的土壤,郑观应则给了香山文化内涵的丰富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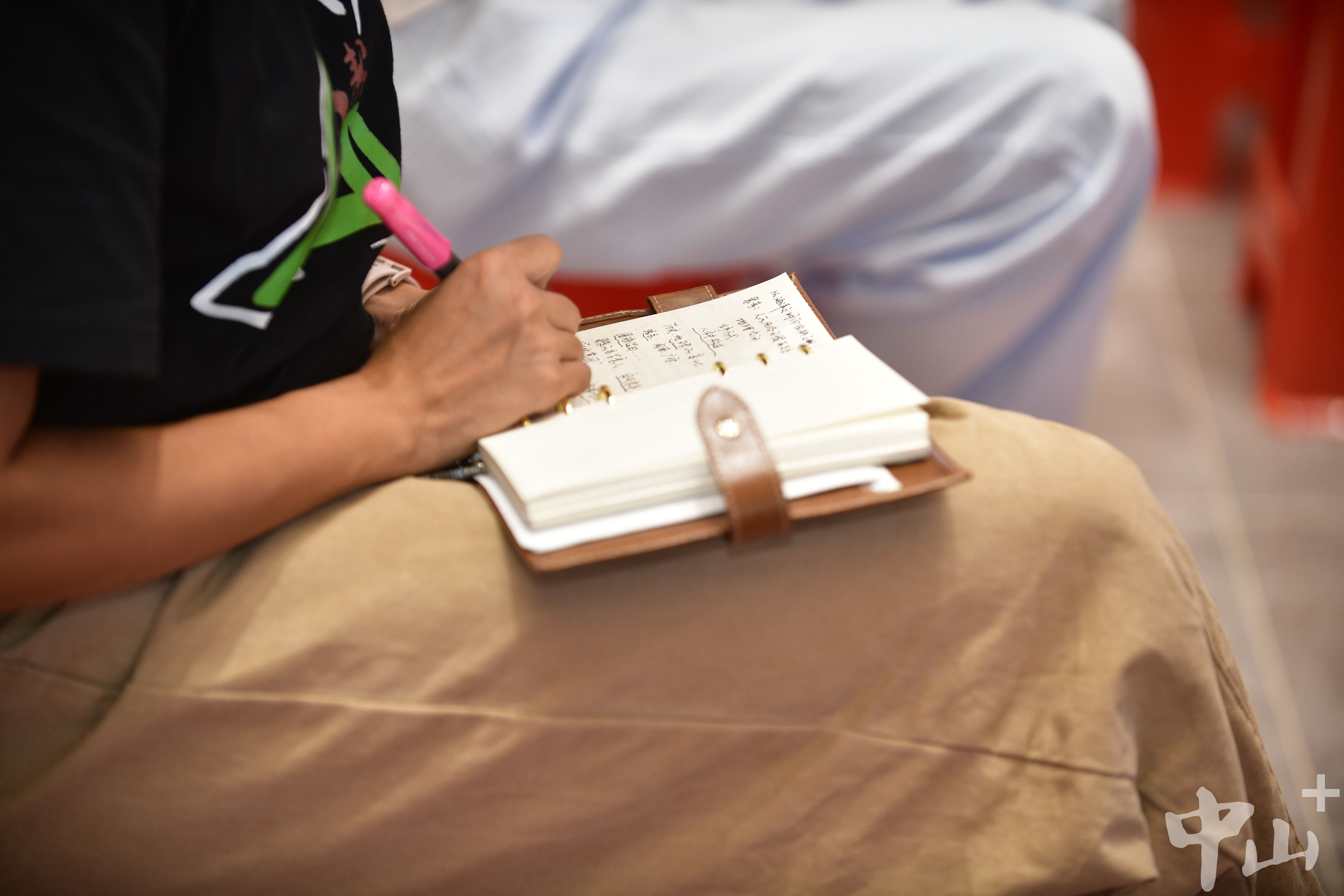
这种交融首先体现在思想层面。“香山文化的包容性,让郑观应能以理性眼光看待西方文明,既不盲目排外也不全盘西化。”胡波教授举例说,郑观应在上海主动与外国传教士交流,却始终坚持儒家伦理;他学习西方企业管理,却把诚信经营作为商道核心。这种取其精华、去其糟粕的态度,正是文化包容性的最高境界。
在冒险创新精神方面,如果说香山先民围海造田是生存层面的冒险,郑观应的“商战”思想则是更高层面的创新。他放弃科举、投身洋务、呼吁改革,每一步都是突破常规的冒险。这种勇气从个体生存延伸到民族发展,让香山文化的冒险精神有了更宏大的格局。
谈及郑观应对香山文化的反哺,胡波教授表示,在郑观应之前,香山文化是地域文化;通过他的思想与实践,香山文化中开放、务实、创新的特质,突破了地域局限,成为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精神共识。
而今天,我们谈论香山文化与郑观应,不是为了怀旧,而是为了汲取力量。这份文化里的包容与开放、务实与创新,这份人生里的初心与坚守、担当与勇气,正是我们当代人最需要的精神养分。
“香山文化至今仍在演变,粤港澳大湾区建设、珠中澳一体化和新移民的涌入,都在给它注入新活力。”胡波教授表示,要传承发展这份文化,不能只做博物馆里的陈列,要像郑观应那样“知行合一”。他呼吁,中山、珠海、澳门三地充分合作,形成文化合力,通过学术化、艺术化、产业化、数字化、生活化等“五化”路径,让香山文化与郑观应的思想走出地域、走向全国和世界,成为激励后人砥砺前行的精神旗帜。
编辑 张英 二审 王欣琳 三审 查九星

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