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月15日,香山书院迎来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。暨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、博士生导师王京州,中山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、秘书长梁斌做客中山市香山书院,共同为读者们带来一场生动的主题讲座,揭秘了位列香山书院“十大典藏好书”榜首的《永乐大典》的编纂传奇、流散历程、现代启示和珍贵价值。据悉,这是2025中山书展·重点特色分会场香山书院的系列文化活动之一。

在历史坐标中了解
《永乐大典》的独特价值
历史典籍版本蕴含着中华民族的智慧、精神和文化,是文明得以生生不息的载体和工具。《永乐大典》作为由明初永乐皇帝敕撰,姚广孝、解缙等主编的一部按韵编排的巨型类书,全书1.1万多册,2.2万多卷,约3.7亿字,有正(明永乐)、副(明嘉靖)二本,保存了14世纪以前的中国文学、哲学、历史、地理、宗教及各种技术等,是明代以前的“文化大集”,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。然而,由于正副二本在后来先后被毁和陆续散佚,今存仅4%左右,目前我们仅能看到存世的约400册。

讲座中,王京州将《永乐大典》与清代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《四库全书》并置,通过“三同四异”的比较视野,揭秘这部旷世巨典的独特光芒。其中三“同”是指官修、巨编、纂集。“虽然三本大集分别在明、清两代成编,但‘述而不作、辑录成编、模块集合、保留原貌’是三者的共同点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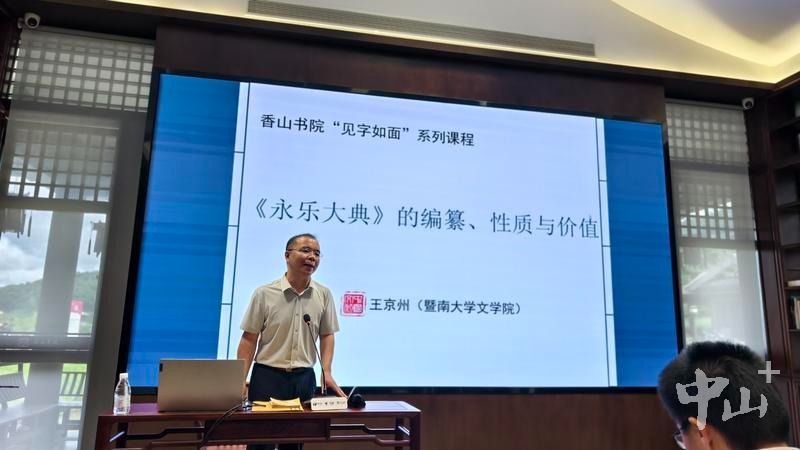
而在版本上,《永乐大典》有正副抄本,区别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铜活字本和《四库全书》的七阁抄本,更为稀少、珍贵。在性质上,《永乐大典》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属于类书,对所收文献内容进行拆分重组,而《四库全书》则是保持原书独立的丛书。在体例上,《永乐大典》独创了“以韵统字,以字系事”的编排方式,依据字的韵部排序并汇集相关词汇典故,这与《古今图书集成》的主题分类和《四库全书》的四部分类法完全不同。
在存佚状况上,《永乐大典》的遭遇更是令人扼腕,正本下落不明,副本历经劫难仅存世约4%,远逊于基本保存完整的《古今图书集成》和仍有四阁抄本存世的《四库全书》。
王京州说,《永乐大典》无疑是一座汇聚中华璀璨文化的宝库。但回望历史长河,《永乐大典》的命运仿佛是一曲悲歌。关于《永乐大典》的流传之谜,目前有多种说法。其中关于正本下落,有的说是随嘉靖帝陪葬明永陵,有的说毁于明末万历年间大火,有的说毁于明末李自成焚毁宫殿;而副本的下落则认为是“毁于庚子之变的纵火和盗取”和“陆续散佚于清官员的监守自盗”。
无论是什么原因,正是这种残缺和遗憾更凸显了《永乐大典》的辑佚价值与学术价值。王京州引用“补人间之缺本,正后世之伪书”的评价强调,因其保存了大量后世失传的文献片段,使得后世学者如钱南扬、罗国威、丁治民等能够从中辑佚出众多珍贵古籍内容,对恢复古代文献原貌、校正学术讹误起到了关键作用。
让大典飞入“寻常百姓家”仍需努力
随着近年来社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视,公众对这部典籍的关注度越来越高,展览和传播活动也日益活跃。
一方面,学界持续在全球范围内搜寻散佚的《永乐大典》残卷,并推动高质量的影印出版,为研究提供便利。另一方面,数字技术的应用更是重要突破。王京州介绍,《永乐大典》高清影像数据库(第一辑)已发布,除呈现《永乐大典》高清图像、整体风貌及相关知识外,数据库还尝试对部分大典内容做了知识标引示范。目前,该数据库在古籍数字化平台“识典古籍”上可以免费浏览,极大降低了公众接触珍贵典籍的门槛。

与此同时,以国内研究《永乐大典》的专家杜泽逊、张升等为代表的学者,也正致力于深度整理与研究,旨在推出严谨科学且便于普通读者阅读的现代版本,其中也包括对残缺内容的探索性复原。王京州进一步说,由于《永乐大典》一出生就藏于深闺、束之高阁,难以为世人所知,几百年来没有很好地起到传播文化、润泽民众的作用。如何让更多古籍文物走出图书馆、博物馆,化作滋养民族精神的涓涓清泉,让人们更加可及可感,仍需要学者和社会各界不断思考和努力。
讲座现场,香山书院读者司兆周分享了她的学习体会。司女士表示,通过王教授的讲解,她对《永乐大典》有了初步认识,对其价值有了深刻体会。令她印象深刻的是,这部典籍对中山的历史细节也有记载,如书中对古代香山的描述为“香山为邑,海中一岛耳,其地最狭,其民最贫。”司女士认为,在信息不发达的明朝,能够将众多地方历史风貌纳入记载,可见其工程之浩大、组织之精密,令人深感敬佩,期待越来越多关于《永乐大典》的研究成果面世,让更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
《永乐大典》是“馆阁体”书法的
代表性开端
梁斌在讲解《永乐大典》的书法艺术特色时,邀请市民读者近距离观摩香山书院的典藏版,方正、光洁、乌黑、大小齐平的字体,如同打印般工整,让人赏心悦目。他说,《永乐大典》全书包含3.7亿字,翻看目前仅存的典籍,我们依然很难看出是由2000多人连编带抄写的作品,其书法正是“馆阁体”书法的代表性开端。

梁斌介绍,“馆阁体”原本是由以欧(欧阳询)体、赵(赵孟頫)体两种风格逐渐演化而来的,解缙、姚广孝等主持编纂《永乐大典》时,为了字体统一、好辨认,强调了规范、美观、整洁、大方,不强调个性,“馆阁体”的特点日益凸显。在《永乐大典》的示范作用下,“馆阁体”日益盛行,再加上科举考试的实用性,康熙、乾隆等皇帝特别喜爱,馆阁体在明清两代备受追捧。
然而,现在一说“馆阁体”三个字,不少人就直摇头,认为这种风格的书体“板滞单调”,甚至把它和“打印体”“江湖体”画等号。“这种认识是有待商榷的。”梁斌说,由于明清两朝的学子为了科举及第,都会努力训练一手“考场通用”的好字,“馆阁体”在当时的官方文件往来中具有很强的实用价值。
随着打印技术的普及,如今我们的书法作品追求“艺术性”大于“实用性”。“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,不能用现在追求书法艺术的标准,贬低‘馆阁体’在当时的实用性。事实上观赏《永乐大典》的书法还是很舒服的,要写得一手‘馆阁体’也是有难度的。”梁斌说。
【统筹】闫莹莹
【视频拍摄】孙俊军
【视频后期】林子晴
编辑 何淼 二审 王欣琳 三审 查九星




